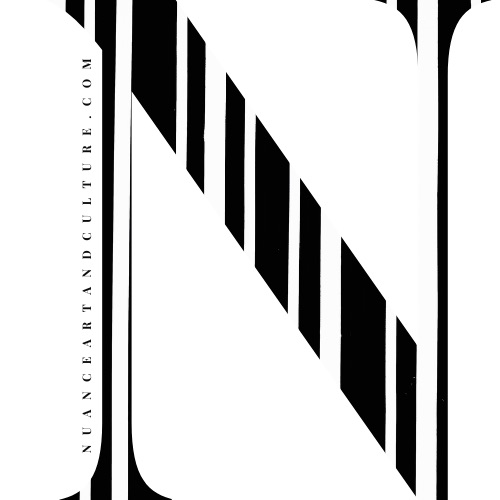《辋川梦忆》

《辋川梦忆》(局部)
戴光郁,宣纸彩墨,74 厘米× 214 厘米,
2011年,图片来源于艺术家。
《夢境,地理,地圖和畫中的輞川》
文/戴光郁
將宣紙鋪展於巨大案桌上,在上面施水、衝墨、敷彩、逐層遞染,手段一如工筆重彩烘染法。反反復復施繪中,一個層次分明,清晰可辨的風景畫作漸次出現。是的,我所描繪的風景與傳奇詩人有關。靜謐,詩化般抒情,空蒙中些許虛幻與超逸,不正是他詩歌創作鋪陳的美學意境嗎?

《辋川梦忆》(局部)
戴光郁,宣纸彩墨,74 厘米× 214 厘米,
2011年,图片来源于艺术家。
《山居秋暝》
空山新雨後,天氣晚來秋。
明月松間照,清泉石上流。
竹喧歸浣女,蓮動下漁舟。
隨意春芳歇,王孫自可留。
《鹿柴》
空山不見人,但聞人語響。
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

《辋川梦忆》(局部)
戴光郁,宣纸彩墨,74 厘米× 214 厘米,
2011年,图片来源于艺术家。
蘇軾先生說,摩詰畫中有詩,詩中有畫。並非虛飾之詞。可是,這次我所畫,並不只為尋求某詩意境而來,我要作的,是為挖掘熏陶詩人詩情畫意那份情懷的自然環境——實則是人文環境,何以鑄造詩人美學精神,詩心何以能與詩境連接,書寫一個凈化心靈,超越平凡世界思想理路的。沒錯,王維山居所在地輞川,屢屢顯影於詩人偉大詩篇,往往也為後來者頌讚,便不是孤立存在的事實了。一如隱逸詩人陶潛“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之高邁情懷,田園詩思想所徵,也並非僅僅體現在某一詩句中,而在其一以貫之地思想追訴中。故而,作為思想屬性的“輞川”,也就超越了地理概念的輞川,也從地圖標識的輞川、人族居住的輞川邁進到思想之維,美學之維,哲學之維的“輞川”。這是絕對美妙,心境可期的思想逸境——或言聖境。豈容泛泛而論?
然而,在思想守持的尋繹中,仿彿夢中尋覓,輾轉勿得,卻又似乎有路可循。現實境況尋詢中的情況是,地理概念的輞川早已不復,更不要說思想理念中理想的輞川。現實中的人根本不認識“輞川”,更不需要詩歌塑造的“輞川”。“空山梵唄靜,水月影俱沉”(〔清〕納蘭性德)的澄明境界、思想沉思哪是現代人要的。我在一位日本學者專著裏讀到,輞川早在文革結束“改革”之初,便為社隊企業改造成不見松林湖泊的破水塘臭水溝。鳴呼哀哉,我的精神屬地毀矣!思想無所依從的世界,正在壓迫奮發向上的靈魂。再敘“輞川”精神所指,難道不是一個思想之喻的象徵!所以我畫輞川,也就賦予了不同方向地指證力量——譬如生態環境(已不僅僅是思想層面人文環境了)。現在,現實中的輞川已畫不出王維詩中的精神關照,正好,跨越地理環境,以德國風景為背景——可以依循的真實場景,巴伐利亞“基姆湖”,作招魂式的“輞川”風物尋夢,不就更加符合超越性意義之思想特質嗎?我將此畫命名為《輞川夢憶》,是為恰當表達這份失卻的真義而惋惜的內心之痛。

《感知地理》展览现场
一幅美麗的風景畫呈現在眼前,美妙無比。作為施繪者,我毫不猶豫地將畫撕成幾塊。是的,我撕毀了它。瘋了嗎?沒有。這是我的畫前計劃,更多地毀壞還在後頭。然後,我逐塊烘染撕壞的畫面,彷彿撕畫行為並未發生。
撕壞畫面,重繪,裁切成無以計數的小方塊,依次排好,再一塊一塊、毫無差錯地貼回至亞麻布畫框(力圖恢復風景畫原貌)。好的,《輞川夢憶》完成,破損痕跡永在。差不多見過此畫的人都說:殘缺之美,好!聽人這麽說,我也不便說更多。只是,“囯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猶然在耳。
批評家查常平在他專著《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第一卷世界关系美学》中將其命名為“戴光郁的破山水”,听起来不十分美妙,却一语中的。在思想层面,破山水概念最早产生于明清鼎革時期的黄宗義、顧炎武及傳山們思想論述及詩創中。“殘山”、“剩水”、“斷岸”之痛不絕於耳,蕩擊心扉。山河之失連帶出“山水”之失的精神創傷,撕心裂肺。鼎革時期的思想巨變,尤為衝擊知識界。思想家率先發問,追詰人文思想與精神守持不可失卻的意義蕩滌數百年,成為思想界可以依循的思想正路。依承於此,我們今天的人靈魂尚未泯滅的話,難道不該繼續發問嗎?
現在,作為“感知地理”藝術展參展作品,《輞川夢憶》不正是為演繹展覽的思想主題而來嗎?如是,我將開懷大笑。
2023年7月29日急就
時在巴伐利亞基姆湖

《感知地理》展览现场
文/康书雅博士
唐代诗人王维和裴迪撰写诗集的《辋川集》,作为一系列呼应式五言绝句,历来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。长期以来,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和学者不仅讨论这些诗歌,还讨论王维本人所作的山水画卷《辋川图》。奥克塔维奥·帕斯(1914年至1998年,墨西哥诗人、作家)与艾略特–温伯格(1949年——,美国作家)合著了一本名为《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》(1987 年)的书,对《辋川图》中单首诗《鹿柴》的 19 种译法进行了有趣的分析。
鹿柴
空山不见人
但闻人语响
返景入深林
复照青苔上
Empty Mountains:
no one to be seen.
Yet—hear—
human sounds and echoes.
Returning sunlight
enters the dark woods;
Again shining
on the green moss, above.
–(译)盖瑞·施耐德,1978年
根据阐释学的接受理论,我们可以了解到,一首诗与其说是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,不如说是在被翻译的过程中被多次重写和改写。这不仅适用于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,也适用于一种文化转译为另一种文化;当一首诗从一个时期流传到另一个时期时,重写再创也会发生。王维的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,而他的画作《辋川图》也被戴光郁两次再创作。戴光郁不只是重现了这幅画,而且将其摧毁并再次重现,让我们关注到这一重新设想并重现原作的历史过程。
——康书雅博士

《辋川梦忆》(局部)
戴光郁,宣纸彩墨,74 厘米× 214 厘米,
2011年,图片来源于艺术家。